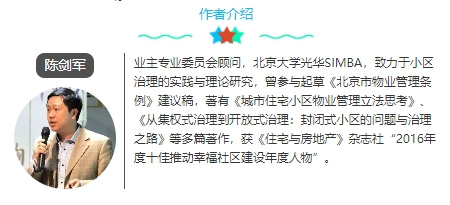专题系列:将物业管理纳入社会治理(三)
社会治理引领物业管理壮大发展(续)
四、社会治理减缓政民冲突
因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属于公共事务与准公共事务范畴,“公信”则是这类事务治理得以持续的核心要素。然而公信的建立,不是只要有了“政府管控”就能实现的。因为公信的实质,乃是各方——包括政府作为一方的——互惠公约的建立与维护。他需要在各方参与、自愿遵守的基础上,共同建立起各方共识的相互透明的“证据体系”(或者说“公据”体系),以持续证明大家在相互互惠中合作,由此公信才能形成。
缺乏公信公据,管控式的城市管理难以建立其可信的官民互惠关系。官民之间很容易陷入难以自拔的互害冲突里。许多小区的业主与街乡的冲突,就存在典型的囚徒困境的特征。
前面的讨论已经知道,在这种缺乏社会组织的管控体制里,官商关系非常密切,官民之间的互惠关系已经被破坏。官员利益除了包括体制内的升迁,还有相当重要的企业给予的经济回报。而居民利益则很简单,就是要长期安居于本地。一旦官员与居民发生冲突(比如政府停止了有可能想更换物业企业的业主委员会的工作)。在缺乏沟通、缺乏公信的情况下,两者都会认为互惠不存在,继续冲突下去是最佳决策。
官员策略的核心是维系现有城市管理体制,这是他的利益来源。官员会认为,只要阻碍业主委员会选举的任务完成,就可以获得领导认同与利益集团的经济奖励。因此不论老百姓是否继续对抗,官员选择对抗策略——阻碍选举——才能确保利益最大化。居民则认为,他们需要建立约束官员、体现居民长期利益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调动上级监督下级、政府监督市场以保护居民利益。要想获得这个机制,居民们需要集体行动展现力量。如果不继续展示集体力量直到机制形成、或者给这个官员足够惩罚,大家就会担心,即便官员暂时停止了阻碍选举的行为,但由于有效保护居民利益的体制没有实现,未来官员欺上瞒下再次行动的可能依然无法消除。这一策略的核心则是打破现有城市管理体制。于是,不论官员是否愿意停止冲突,居民继续采取对抗策略才能确保利益最大化。两方立场差异很大,又缺乏中间的沟通。策略选择的结果,就是各自坚持原有对策,于是两方就继续陷入更为激烈的冲突之中。
破除这种困境的办法,只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社会组织。首先,在社会组织强大的情况下,官员的升迁要依据社会的意见;而寻租则受到高成本高风险的制约;获得社会认同的官员,可以有更好的长期当政与发展机会;个人待遇亦可以回归市场化。因此,官员的收益,不再是仅仅来源于官僚体系内部与市场寻租。于是官员增加了与大众沟通的愿望,大众对其信任亦经由社会组织的公开监督而建立,由此具备了互惠合作的基础。同时,社会组织克服了居民高度分散、利益多元、缺乏必要监督知识、与政府之间难有日常交往的不足,形成了稳定的信息交流、矛盾弥合的渠道。社会组织为谋求自身长期发展,客观上形成了组织理性,亦大幅削弱了谣言的聚众感染力。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之作为民官相互沟通的一个可信任的载体,并使得这个载体成为民官之间的互惠的“共同利益”,在打破体制与维系体制之间建立起可以动态调校的机理,才能起到对政府偏执与对大众偏执的回牵作用。
五、社会治理促进物业管理创新
我们都知道,创新可以带来更多收益,带来更多可以选择的转型路径,可以极大缓解各方转型压力。但是管控式的城市管理,人们被权力隔离而沙化,相互交流少,信息中心亦少。缺少信息中心,人们难以接合,商机难以规模,创新受到阻碍。因此,在管控思维依旧强大的物业管理行业,创新还是得不到大发展。社会成长带来创新的根本原因,是各类社会组织成为社区里的可信的“信息中心”,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新商机的诞生。
历史上,人们在居住在传统的乡村,往往以一棵古树,一所公院,作为村社交流的信息中心。但在进入城市小区后,钢筋水泥与管控式权力隔离了大众。本来就面积缺乏的文体中心也被开发商拿去出租。幸好有了社会成长,也得益于互联网的帮助,被钢筋水泥隔离的一盘散沙的居民业主,开始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为中心重新进行交往。由于社会组织更为公开透明,这些交往更为可信,因此大量兴趣团体蓬勃发展。每一个兴趣团体就是一个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中心。这些中心的建立,大大降低了商业服务的交易成本。新商机经由社会组织而凸显出来。早期各种OTO的失败,就是没有抓住社会组织乃是社区信息中心之要点,没有看透社会组织的商机魅力。
事实上,物业企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天然的近距离的特点,如果物业企业亦可以获相关部门批准、获得相关资金支持而直接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混业促进了资源整合,更多的商机可以出现。在与重庆本地多家物业企业调研中得知,物业企业自身人力资源特点,可以有许多创新服务。比如,保洁工人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3个小时完成。如果能组织好余下的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许多家政类工作,比如代购菜品,代洗、代切蔬菜,代为照顾老人,代接学童等等。不仅如此,将多个小区、多个单位的维修工组织到一起,通过互联网下单、接单,可以更好满足家庭维修的需要。这些服务,即可以方便业主居民,又可以显著提高物业从业人员偏低的工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营造工作,比如社区调查、户口调查、互助培训、一米菜园、垃圾分类、义务消防队等人、文、地、产、景类事项,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亦可以组织业主代表或居民来完成,而不是只有居民组织或特定的民非机构才能承担。
民政部应进一步开放政府采购主体范围,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企业纳入其中,好处还不止是商业创新,亦有社会创新的意义。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原本就是公共事务处理者,原本就是社会工作者,他们进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接受民政系统相关培训与工作规范要求,转型为规范的社会企业与社工,极大充实社会治理的力量,这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政府、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都可以因此而达到共赢。但是,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物业企业与业主委员会被归属到住建部的管辖范围里,一方面住建部的一些官员不支持物业企业涉足社会服务,认为他们荒废了主业,另一方面又被民政部排除在“社会治理”的政府采购的合格主体之外。这种管控思维带来的行政管理,人为造成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与社区营造的各类主体的隔离与对立,在阻碍了社会治理发展的同时亦阻碍了物业管理的发展,应当尽快加以改变。
社会治理成长带来的物业管理的创新,还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谁能更好地组织业主居民,谁就有了新的商业力量。物业管理纳入社会治理所带来的创新,甚至可以极大扭转物业企业与开发商之间的不对等的行业关系,从而极大激发优秀物业企业的转型热情。比如优秀的阳光的物业企业,可以通过对老旧散小区的“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房地产领域。所谓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就是通过将居住地上的业主、居民组织为一个整体,政府通过投入土地成为联合开发人与其合作开发。开发的成果,一部分属于业主居民就地改善生活,一部分属于政府用于满足周边社会需要,将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主要的开发目标之一。这样一种房地产开发的方式,叫做社会价值型开发。
当下的老旧小区,政府需要不断投入资金维护维修。北京一位住建委官员曾谈到,老旧小区的维护维修资金越来越多,未来将拖垮北京的财政。随着年头越长,政府投入维护维修的资金越多,拆迁重建的获益就越低。另一方面,没有组织起来的分散的居住人,都在眼巴巴等待政府拆迁补偿。甚至在北京,有的等待拆迁的小区业主居民,宁可污水管堵塞带来污水泛滥,也不同意甚至阻碍政府维修损坏的污水管。他们认为,政府投入维修就是为了拖延拆迁。只有小区越破败,政府出于“爱民”的压力越大,才会加快拆迁步伐。但是拖延的时间越长,需要的补偿条件越高,拆迁组织的难度就越大。而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趋势放缓,成本过高的拆迁补偿给开发商亦带来巨大经营风险,于是拆迁变得遥遥无期。而这些老旧小区,又往往处于城区内,周边商业发达,公共服务如停车、文化场所等严重不足,增建的需要迫切。因此,我们换个思路来解放老旧小区,采用“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方式。政府不再将业主居民当做分散个体,逐个谈判拆迁补偿,而是在物业企业与业主组织的帮助下,将业主居民们组织成为一个整体(比如每家出资建立老旧小区“社区基金会”)。政府不再走单纯卖地的财政道路,而是将“土地管理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资源注入到这个社会组织,作为他们的“联合开发伙伴”。业主、居民自我组织资金、组织拆迁、组织开发。这个时候,越早拆迁,居民获得的居住改善的收益越大,而政府亦可以通过土地作为投入获得安置房与停车位用于满足周边公共需要。尽管政府的土地收入与税收降低,但是政府获得了一大批社会资产,大幅降低长期维修资金支出,大幅降低周边大量民间纠纷的公共管理支出,综合而言利远大于弊。这就是在社会组织发育后,大家共同走出的“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的道路。在这样的新型开发方式下,参与其中的物业企业亦要承担社会责任,其账目公开,诚信经营,接受每一个业主居民的监督。此刻的物业企业,就不再是开发商的附庸,而是政府帮助业主组织的重要助手,甚至成为业主组织面对开发商、购买开发商服务的甲方专家,行业的甲乙方关系出现逆转。而老旧小区,亦不再是肮脏、亏损、混乱的代名词,转而成为资本追逐的金矿。老旧小区房价的回升,也为那些不愿意参与共建的业主提供卖掉老旧房屋的机会。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政府通过创新,建立并扶助老旧小区的自治组织,通过自治组织的成长而促进物业管理沿着产业链前置化发展。
另一方面,当今社会,老年人还有一定流动资产,许多骗子利用各种高息回报诈骗老人。而老旧散小区里老人较多,大部分房屋业主是从单位房改房时候购买的房屋,到了现在许多人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采取社会价值的土地开发,可以融入他们的资本,比如“一家20万,政民共建新家园”等方式。将每家每户投资与政府土地投入相结合,成立联合法人主体,以信托方式交给开发机构开发,至少可以构建一个安全的改善社会、造福众人、回报均衡的稳定投资机会,给现在的老人们与未来的老人们一份有意义的安全回报。
不仅老旧小区可以“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一些国营单位开发后余留的依旧居人的边缘土地亦可采取,许多老百姓居住其中苦盼政府拆迁。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笔者曾经调研过两块平房居住区,都是国营单位土地,都位于良好地段,各自仅有几十户居民居住。由于居民长期苦熬,因此拆迁补偿要求高。但因为土地面积不大,传统开发方式的经营效益不高,企业也没有拆迁开发的积极性。两块居住地的市政与卫生很差。旱厕、垃圾站里苍蝇密布。下雨后,排水系统损坏,居民只好在家里使用水泵抽水。有其他住房的居民将此处出租等候拆迁。最为弱势的居民只好苦熬。事实上,其中一块土地对面就是清河五彩城商圈,经济发达,高楼林立,用地紧张。如果该地块从国营单位划给以居民为主组建的社会组织,由街道与社会组织与物业企业协助做好规划进行“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不仅居民们可以尽早过上好日子,该地块亦可以为周边停车紧张、商铺不足、公共文体场所少带来很好社会与经济效益。而类似这样的零星边角土地并不少。
不仅零星边角土地可以进行社会价值型土地开发,政府的老旧楼亦可以进行。比如一些街道办或事业单位或国营单位或其他政府公楼,位于各个街区较好地段,本身就是周边公共服务紧张、停车位缺乏、文化活动场所不足之地。仅仅用来政府办公,行政资源的社会效用发挥不足。政府与社会合作,将周边业主居民组织起来联合投资,将这些楼或者拆建、或者改建、或者增建,使得停车场所、文体空间、平面或垂直绿化得以增加以满足周边需要。
综上所述,将小区物业管理纳入到社会治理,将有效去除阻碍物业管理发展的体制障碍,特别是管控式城市管理体制的权力扭曲,极大释放物业管理的发展空间,对行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未完待续,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