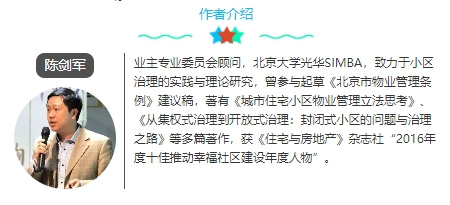专题系列:将物业管理纳入社会治理(一)
一、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物业管理的发展需要
早期的物业管理基本由单位与政府负责。伴随住房商品化,商品房小区的物业管理开始走向市场。随着物权法出台,业主们开始依法行使对小区的共同管理权。于是,物业管理从政府主导的单一主体格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格局。主体多元化产生了对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治理”小区而非政府或企业单边“管理”小区的需要。然而当前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强调“管理”而忽略“治理”,强调“市场”而忽略“社会”。因此在其基础上产生的“行业管理”,以及后来提出的“属地管理”,都无法满足物业管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无法解决各个社区普遍存在的物业管理问题。这就是全国范围内物业管理出现大量冲突的城市管理体制根源。
1996年3月27日上海市召开“城区工作会议”并下发《关于加强街道、居委会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政策意见》,开始着手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并引起全国的仿效。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核心思路是管理权力下放。通过向下创设新的行政层级,向下转移行政权力,调动基层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比如1个市长下放权力给10个区长,每个区长再下放权力给10个街道。如果1个人可以完成1个亿的项目,那么在三级管理后,就有110人可以完成110亿的项目。在土地经济的早期阶段,这种划小土地片区、权力层层下放的方式,对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土地经济发展达到足够规模,大量的土地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之后,公权力如果不适当收回,公权人数量越多,公权人滥用权力造成与私权人之间的冲突就越多。比如社区,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控体制下,街道乡镇与条条部门的行政权力通过物业企业与居委会下沉至小区,业主们要接受物业企业与居委会的管理。然而,物权法赋予了业主们通过共同表决来共同管理的自主权,无须政府额外行政许可,更无须物业企业与居委会批准。相反,物业企业作为受聘服务人,反倒受业主们约束,甚至由于服务不佳而被撤换。即便街道乡镇做出的决定,如果违反相关法律,侵犯业主权益,业主们也往往经由行政复议、诉讼而撤销之。于是,业主们的治理权利与街道乡镇的管理权力,不断在具体事务上出现冲突。
不仅如此,透过物业企业、透过小区可以预见,这种完全建立在管控思想上的城市管理体制,由于社会无法参与其中,更大更多的弊端还将不断暴露出来。举一个例子,北京丰台区一台供暖锅炉爆炸,八个小区冬天里停止了供暖。业主们维权发现,他们缴费购买的供暖服务,并非想象中由可靠的市政机构所提供,其实是由一家小型私人机构提供。这种经营模式早已在各地大量采用,叫做公共服务外包。但是这种外包,既然属于公共服务类型的,既然涉及千家万户,却没有任何渠道向社会开放监督,甚至连相关受益人都毫不知情。这种由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由于撇开了社会的参与,其最主要的弊端是由于企业与业主的沟通中断,极易导致业主与企业陷入互害困境。在改进服务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监督服务的路径均被堵上的情况下,居民们认定企业公信不足,以不缴费来对抗。而企业在供暖费收缴不足的情况下,宁可降低服务或向政府索要补贴,也不愿意改进与业主的沟通,更不愿意接受社会监督以提高公信。于是,双方陷入不缴费与降低服务的恶性循环之中。大量财政补贴都为此浪费。更重要的是,一旦企业向政府索要的补贴不足,设备维护维修投入就会下降,运营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由政府主导,仅仅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商议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由于失去了社会参与带来的沟通与监督,服务普遍下降,最终政府买单。公信的建立,不是只由“政府管理”就能实现的。政府管理越独大越自负,越把自己做为“公信”的最佳背书人,越来越多的包袱就会交给政府。事实上,公信树立的实质是公约的建立与维护。他需要多方参与,通过信息的充分分享,共同建立起各方共识的开放透明的“证据体系”。有了证据体系,公信才得以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强调了政府管理、强调了市场经济,忽视了治理、忽视了社会,因此基于多元参与才会形成的“公信”就难以成长。公信不足,政府的管理、市场经济的发展,亦难以继续前行。
不只是供暖,物业管理作为一个综合服务体系,其内部包含大量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或准公共服务性质的专业项目。每个专业项目都由不同的行政机关加以管理,比如住建、房管、人防、消防、安监、交通、市政、通讯、街道、公安、气象等等。因此,我们从小区出发,透过物业管理,可以发现更大的城市管理的困境。这些条条行政部门通过部门立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各种资质管理、资产代管与行政执法等手段有力地单边地管控了这些行业领域的核心资源。在管控思维下,这些领域的社会组织发育弱小甚至尚无踪影,根本谈不上对条条部门的监督。结果政商关系密切,腐败严重。由于行业经营权操纵在政府手中,企业宁可损害消费者利益也不会减少官员利益。这种行政管控缺乏公正与创新,越来越被看做“规模不经济”、“道德非楷模”的代名词,规模越大就越发没有给大众带来安全感与幸福感。
于是,人们心中被压抑许久的社会治理激情,通过物权法透过小区治理而释放出来,极大地冲击了乃至冲破了原有的官商利益关系。越来越多小区业委会开始主张将各种资产、资金、资料、资源从物业企业、开发商乃至各个行政部门手中拿回来。越来越多业主居民开始认识到,问题根源不在物业企业,而是源自各个行政部门单边管控下的各种公共事务与准公共事务的不透明。于是大量的变革呼声从围绕物业管理的各个行业都冒了出来,不论是人防车库的政府外包信托化,还是供暖行业补贴与管理的公开,还是自来水外包经营的公开,还是其他更多......。更多业主居民要求这些行政部门的单边行业管理都必须转变为社会、市场与政府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没有建立在“社会治理”这一牢固地基上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已经走到了摇摇欲坠的尽头。
针对城市治理体制,重庆市南岸区做了探索。区政府推行的“三事分流”获得了民政部社会治理创新奖。在社区范围,通过三事分流,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协商,区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各自责任,将街道向社区的权力传递在纵深方向上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这种收权,是在社会参与下的共同“治理”的成果。更进一步的尝试,还可以在两个方向进一步拓展与提升。一个是将三事分流从社区范围扩展到街道范围。通过与更多社会组织交流,将街道的市场职责进一步缩减,修复社会公平的职责进一步加大。其次,要将“三事分流”实践,从事务分类进一步提升到共同公约。当下“三事分流”的前提,是一个拥有“治理”情怀的政府。他不僵化,可以与社会对话;他具有弹性边界,可以与大家协商各自的责任边界。但是要使得这种政府状态持续,而不是人亡政息,就需要把治理原则落实到各个社区的“基础法”里,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在每一个小区、每一个社区里,都播种下政府、社会、市场联动治理的“公约”种子。只有当社会得以发展,只有将物业管理纳入社会治理,现在看到的各种问题才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二、将物业管理纳入社会治理是公众对城市治理体制的需要
两大阵营越来越明显。一个阵营是部分地方政府、开发商、物业企业,他们对业主主导治理表示不满或甚至恐惧,各种指责、各种不作为与各种打压层出不穷。政府持有的有利于社会治理的关键信息不公开不提供,历史上形成的不当利益继续纠缠而不摆脱,对业主治理中存在的自我调整的现象,动辄干涉乃至借口阻止。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小区走向良好治理,随着越来越多城市接受治理,这个阵营的声音,越来越苍白无力。
另一个阵营则在高速成长之中。首先是业主组织自身在努力学习而快速成长起来。许多城市的业主委员会们运用互联网,不仅建立了本地的线下论坛,定期相互学习,他们还与其他城市的业主委员会们联系到一起,构成了一个近4万小区覆盖量的“业主知识共同体”(部分情况可参见附表一)。在这个群体之中,有普通百姓有政府官员,有高级律师有资深法官,有企业家有教授学者,有媒体有居家妈妈。甚至还有许多物业经理人,还有开发商。同时,一大批专业民非组织、专业第三方评估机构,发挥他们在业主组织与物业管理的专家作用,在这个群体中得到认同飞速成长。事实上,业主是知识宝库,业主是专家海洋,业主是大众桥梁。他们覆盖各行各业,遍及各个层次。他们不论自身背景如何,都在“业主知识共同体”之中相互分享经验、相互学习社区治理知识、相互探讨理性治理。他们是社会腾飞的巨大宝藏。
一部分开发商也认识到治理的好处,比如万科,据了解其76%以上的小区已建立了业委会。一批开发商甚至主动将物业服务合同从不透明的包干制改变为主动向业主们公开账目的透明的酬金制乃至信托制。这些地产商借助社会参与的监督与沟通协调作用,可以更好地管理多个项目,小区物业不再是他们不断补贴的黑窟窿。更多物业企业则主动转型,公开支持社会治理,挑选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才进入。甚至有的物业企业积极探索“阳光清单法”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重新定位自身为社会企业。主动向社会治理转型成了行业竞争的有利武器。与此同时,法院法官们对物业管理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法院判决更为公正。在《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立法预调研的相关会议中,一位法官说: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物业费缴费率上升了。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极大地支持物业管理领域社会治理化的发展。
可喜的是,一部分城市政府开始探索通过发展社会来扶助业主组织成长,来解决物业管理问题。一些城市建立了业主委员会协会或业主委员会联合会,如宿迁、东营、青州、温州、顺德,如省会城市的沈阳、直辖市的天津。宁波市的业委会协会正在筹备,而杭州、深圳、上海则先从区或乡镇开始试点业主委员会联合会。街乡的试点就更多,许多城市的街乡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联合会,各种相关沙龙则无法一一列举。武汉则后来居上,政府带头、全市行动、干部参与。政府将业主大会设立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作为街道乡镇的绩效考核指标,要求在依法符合成立条件的小区,按照100%覆盖之目标,限期完成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在政府带头组织人、财、物、资源向社会大转移的推动下,不到一年时间,普遍成立业委会的阶段目标就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随后的工作是物业企业向业主大会完成四资(资产、资金、资料、资源)移交工作。而湖北宜昌,则紧跟其后,也宣布业委会全覆盖之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办国办的文件,也将业主委员会、业主与居民委员会、居民等并列纳入了基层民主协商的主体范围。这一阵营的声音,越来越有力。
事实上,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努力,为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领域的活力,此刻已经到了由量变转而质变的时候。这种发展力量,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无法遏制。小区、社区,只是这巨大火山的一个主要喷发口。由于业主作为财产共有人,天然存在着与建筑物等共同财产的依赖关系,同时也天然存在着与其他业主的共生关系。因此看似奔流的火热的社会熔浆,并非摧毁一切,而恰恰相反,是为社区长期和谐而极大努力地修复、扭转、引领、提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当有关系。因此,作为地方政府而言,唯有顺势而为,采取“政府带头扶助社会成长”的根本策略,变革传统城市管理体制,积极引导、运用这一发展力量,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注:未完待续,敬请关注!